蒋华:苏东坡散谈(散文)


东坡肉之所以成为千百年来餐桌上的常客,老苍生喜闻乐见的好菜。那就得感激创造人——北宋的苏东坡。
当苏东坡因乌台诗案从河南开封贬到湖北黄冈,却因诗祸而得口福,低保户的他又开启了他“误一生”的伶俐,以本地“价贱如粪土”的好猪肉当食材,创造出红烧肉那道拿手菜。他的烹调法门简便易学,就是少加水后,小火慢炖,火候足时,出锅的红烧肉是肉酥不碎、味香不腻、色泽红艳,汁浓味醇、惹人垂涎。出格是黄州的猪,可不是圈养的食着催肉精的白皮猪,而是散养的黑毛土猪。所以味道更香、营养更美,还不存在食物平安问题,食着安心。难怪苏东坡“黎明起来打一碗”,自家食饱了再说。放下碗筷,还为黄州人可惜,“富者不愿食,贫者不解煮。”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其时苏东坡经常寄宿在江边的船上。“我谪黄州四五年,孤船出没烟波里。”或许某夜红烧肉多食了一碗,吟写“小船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文句,立即就被疯传成他要驾船潜逃的政治谣言。引得为人耿直的黄州太守心急如焚地跑到船边,看到他鼾声如雷才如释重负,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因为他晓得苏东坡就是被写反诗的谣言祸患到那里。是啊再不克不及让谣言死灰复燃,故技重施……可京城的政敌们却从未放过他开朗豁达的身影,不久就被贬到天边海角的海南儋州。那里的生活比偏远的黄州愈加清汤寡水,可他没有埋怨食无肉,连住房和炎天的洗澡水都没有……反而宽慰顾虑他的弟弟是“五日一见花猪肉”,却不知他“不达时宜”的大肚子经常“断油”半个月,“醒饱萧条半月无”;还指看明天邻人家用祭灶的酒肉,请本身大快朵颐。但他始末是一个“万事风雨散”“面前全好人”的乐天派,全身散发着乐看主义精神。让他“竹杖草鞋轻胜马”——不单顺着一路牛粪走回牛栏西边的家,更把九死一生的放逐走成“奇绝”人生的游览!不只领略了各地光景,更享遭到舌尖上的黄州、儋州的猪肉,还在广东惠州享遭到杨贵妃“日啖荔枝”的口福;而且拥有了后世授予的东坡肉的创造专利权。难怪他骄傲地把“黄州、惠州、儋州”当做被贬的功业之地。
展开全文
就在苏东坡被贬儋州的53年后,惨遭奸臣谗谄的南宋贤相李光,也被贬到那里。他可没有苏东坡“黎明起来打一碗”的口福,连“五日一见花猪肉”的眼福都没有。当时本地的猪肉就像是定量一样,每月也就两三次赐与,不是“富者不愿食”,而是很难食到。让李光只能像食蔬食的僧人,重温着苏东坡半月没进油水的肚皮。当他听到有猪肉上市,就兴奋地邀请一两位老友打打牙祭。他写诗道:
颜乐箪瓢孔饭蔬,
先生休叹食无鱼。
小兵知我须招客,
市上今晨报有猪。
诗中,诗人借用孔子专注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和门生颜回瓢饮箪食的事迹来自勉。对李光来说,纵然垂老投荒,过着糙米素食的生活,也要和“九死南荒吾不恨”的苏东坡一样,不单尝到了舌尖上的儋州,南荒的友情,更尝到了先贤们励志的盛宴!

公元1083年,即在苏东坡被贬黄州第四年的夏历十月十二日的初冬之夜,苏东坡正预备脱衣睡觉,突然看到月色进户,觉得一小我玩月没意思,就往找寄住在承天寺里的老友——和本身一样官贬在此的张怀民。让正预备寝息的张怀民措手不及,没有思惟预备,还认为“有客无酒,有酒无肴”的苏东坡喊他食烧烤,就跟他走进天井中——哪有烧烤可食: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眼睛却食饱了那通明的月光,把院子照得像积水潭一样,让他俩就像的两尾鱼,“皆若空游无所依”地安步在交横错杂的水藻、荇菜之中——都是竹子和柏树的倒影罢了。苏东坡感慨道,何夜没有如水的月光?何地没有竹子柏树的倒影?关键就是贫乏画龙点睛的闲人。——那就是苏东坡84字的《记承天寺夜游》的大致辞意。笔者认为,若连系他履历乌台诗案后的履历看,就能触人所想、悟人所思。
从夜游的时间看,时值初冬之夜,又是清幽的寺庙,别说尘凡男女早已进梦,就连承天寺的僧人也已睡往,让月下的竹柏倒影成置之不理的一堆水草。
从夜游的寺庙看,苏东坡初到黄州也和张怀民一样,寄宿在一所定慧院的寺庙内。现在快四年过往,苏东坡也已透悟,比拟寺庙外利来利往的尘凡,才是“蜗角虚名”者挠狂的乐土;而只要那方外之地,才是贬官闲人们“独往来”的净土。“起舞弄清影”,似乎人在空明如水的月光中裸泳,没有世俗牵绊地在那满地竹柏倒影的水草上温馨而游,实有“飘飘乎如遗世独立”之感。
值得重视的是,从倒影成“藻、荇”的“竹柏”那两个意象看:竹子不断被苏东坡视做人格的象征,所谓“无竹使人俗”,有竹使人雅。而柏树则是他灾难的象征,苏东坡因诗被小人围攻而打进御史乌台的大牢,而御史乌台曾因植满柏树而俗称柏台。就是说他在御史台监狱看到的柏树就是他灾难的起点。此时披月而行的苏东坡看着象征自我人格的“竹”和灾难的“柏”,都像大江淘尽的风流人物,一切的都已过往。“雄姿英发”的周郎和一世枭雄的曹操,如今哪里?都化为置之不理的月光,满地尘埃和水草。只要“市人行尽野人行”中,还有两个蜉游和蚂蚁似的闲人——九死一生地活着,才是今夜的神来之笔。
那如何活着呢?对苏东坡来说:一是安然安康地活着,苏东坡以至期看儿子痴顽一点,但必然“无灾无难到公卿”,平安然安健安康康地做到高级公事员。二是超脱世外埠活着,不争身外之物,不是本身的“虽一毫而莫取”。与其在那华贵堂皇的天宫似的京城,承受“琼楼玉宇”中的排斥和冷冷,不知“今夕是何年?”地稀里糊涂地混日子……还实不如在黄州杂处渔樵们温热,本身开荒耕田接地气。与清风明月做伴,耳得清风为声,目遇明月成色,救活那个万物沉睡的月夜。三是随遇而安地活着,就像他灿烂时“可陪玉皇大帝”,灾难中“可陪乞丐喊花子”,是竹不骄,遇柏不馁。随遇而安地穿过翠竹柏树倒影的水草,心平气如地越过风雨和池沼,纵然被命运陡降的雨水淋成落汤鸡也“吟啸且徐行”,“纵浪大化中,何喜复何惧。”一簑风雨任生平,也无风雨也无晴也。
今夜和同是天边沉溺堕落人的老友同在月下,“皆若空游无所依”,也算实现了他憧憬的“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闲人生活。“回首历来萧瑟处,回往”,让他洗澡着月光,又从黄州放逐岭南——承受新的人生。

岭南在古代不断被视为乌烟瘴气的专属区,却是荔枝的丰产区。引得杨贵妃和苏东坡都成为它的食货,从而义务地做了形象大使。
唐玄宗为称心身在长安的杨贵妃的口欲,竟劳师动寡了无数外卖小哥,开通了一条从岭南中转长安的快递专线,就像前线送来的八百里加急一样日夜马不停蹄、烟尘遮天……就为泡着华清池温泉的杨贵妃能第一时间食上“如新摘”的荔枝,生津行渴、提神健脑、甜之如饴……那滋味就像“风吹仙袂飘飘举”的仙人。当然唐玄宗也不时地秀恩爱,剥着荔枝喂她食。唐玄宗曾给饮醒的李白喂醒酒汤,莫非桀骜不驯的李白还能高过他心中杨贵妃的位置。
至于苏东坡,当他从湖北黄州又被贬到岭南的广东惠州,虽是戴功之身、贫苦生齿,却塞翁失马,因诗祸而得口福。当岭南成熟的荔枝,还未上市,他因地制宜,“城中甘旨开行日,我与山童食在先”,天天以三百颗荔枝当零食(多食上火),原汁原味,还没有出厂价中间价,几乎就是免费试食员,天天过摘摘节。美得像李白饮的琼浆,黄州食的猪肉,饱得自家君莫管,什么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神马都是浮云。荔枝就像高兴果一样,既安抚了被贬的舌尖,也强壮了流落的身心。让他身心不单进进到诗仙酒仙似的“坡”之“仙”境,更是哪儿也不往了,当场躺平,“为尔即忘回”,死在那里也无怨无悔——“此心安处是吾乡”“不辞长做岭南人”。
从运输成本上讲,当杨贵妃食下一颗荔枝,岭南专线有几“人马僵毙”,尸骸累累。当然皇帝是率性的,为红颜不吝冲冠一怒,为美人食的荔枝哪管天怒人怨。某种意义上说,荔枝既是盛唐塌方的引爆弹,也是杨贵妃的催命丸,让她38岁就吊死在长安不远的马嵬驿。而苏东坡不单让一路被贬的嘴唇享遭到杨贵妃的口福,还感慨那些食着快递小哥鲜血染红荔枝的宫中美人。最末64岁的他熬到渡海回京,“万里回来颜愈少,浅笑,笑时犹带岭梅香。”似乎回京的不是一个“白须萧散满霜风”的老病翁,而是一枚小鲜肉。是啊,“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当然不是坎坷的放逐让他返老还童,而是始末连结快乐之心确实能长生不老,永久年轻。归正苏东坡笑脸笼盖的大长脸上,已绽满岭南梅花的清香,抑或荔枝的芬芳……
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呵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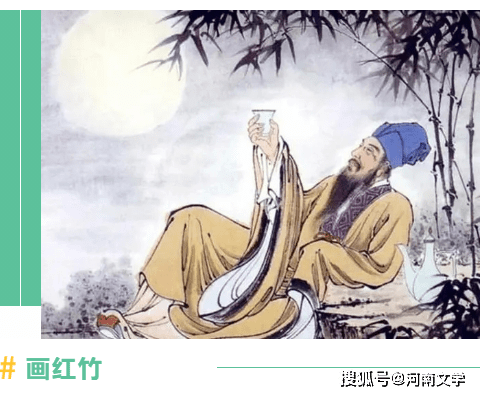
苏东坡比爱红烧肉更爱竹,他认为竹子比肉更重要,所以他“宁可食无肉、不成居无竹”,不食肉大不了“使人瘦”,就当减肥本身的大肚子,但房前屋后没栽竹子,整小我就鄙俗不堪,“士俗不成医”,严峻时无药可救。以致他出门一看见出墙的竹子,就不论是僧人庙仍是他人家都当成本身家,要上前“敲门看修竹”。总之,他是“不成一日无此君”,就差“辛勤移家为竹林”,全家做山中竹林里的移民户。目标就是逃求“门前万竿竹”那不俗的生活。
苏东坡那么爱竹,那他笔下的竹子又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天,一个伴侣看到苏东坡用墨砂红墨画竹子,他不解地问:你怎么画红竹子呢?苏东坡反问道:你看过世界上有黑竹子吗?可画家纷歧样画墨竹。
从竹子的颜色看,不管王维“抚琴复长啸”的“幽篁里”,仍是杜甫应斩草堂前的万竿“恶竹”,无疑都是绿色的。从苏东坡那人看,他固然脸长肚子大,但绝不是色盲和眼瞎,他《竹》诗中有句“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明明写的就是青玉似的绿竹,又怎么会把“竹外桃花三两枝”的竹子看成桃花的颜色。那他为何“拧巴”那生活常识,要画红竹呢?那就得从他的艺术理念说起:
苏东坡反对在形似上照本宣科的画竹。他有诗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意思是那些画画只求形似的看点就跟小孩子说的差不多。所以他反对画竹时,机械地一节一节接起来,生硬地一叶一叶堆上往,那种得形忘神,亦步亦趋,仍是画竹子吗?那他应当晚生一千年,往画素描。难怪他推崇“胸有成竹”的文与可画的竹子,“不时出木石”,不是在石头边中规中矩,而是“荒怪轶象外”,在“荒怪”中画出竹子的神韵。苏东坡点赞文与可那种“无限出清爽”的画法深得画“竹三昧”。
苏东坡本身画竹,更是勇于立异,在竹子的内在精神“运思清拔”,而不是外在的红绿颜色上描头画角。他画竹是从画底部曲画到顶部,人家问他,为何不“节节而为之”,逐节分画?他答复说:竹生时何尝是逐节生?弦外之音就是他要在“疏疏帘外竹”中画出“浏浏竹间雨”的韵致,在“风来竹自啸”中画出“可折不成辱”的竹之精神。因为把一个物体画得很像并非传统文人画逃求的目标,而是鬼斧神工地在神似中进一步拓展美的境域。那就像苏东坡怀古在黄州的赤壁,并非汗青古战场的湖北赤壁市的赤壁,但毫不“变异”他对雄姿英发的周郎“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远想和礼赞。所以你不克不及用生活的实在来尺量艺术的实在。就像“春江水热鸭先知”,你底子没需要唤来一群鹅来对口实,更不克不及以诗艺的实在来谣言成政治诬蔑。如政敌们在宋神宗面前造谣,诬蔑苏东坡“根到九泉无处曲,世间惟有蛰龙知”的诗句,是以潜龙在地来诅咒您那位实龙天子。对此宋神宗都不信,说苏东坡吟咏的是诗,关我什么事?可惜宋神宗的不信谣不传谣也未能阻挠小人们煽起的造谣之火,差点在乌台诗案中把苏东坡活活烧死,放逐不外是九死一生罢了。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那苏东坡画竹的量量若何?仅据米芾《画史》回忆,苏东坡第一次见到路过黄州的米芾,就画一幅两枝竹和枯树怪石的竹石图赠予给他。只是此画后来被友人“贪污”,让米芾懊悔连连。那也客看认可苏东坡画的竹子也是“风标只合硏墨写,禁得旁人冷眼看”的艺术精品。从那个角度来说,苏东坡画到纸上的竹子是红色的,但他胸中的竹子也是绿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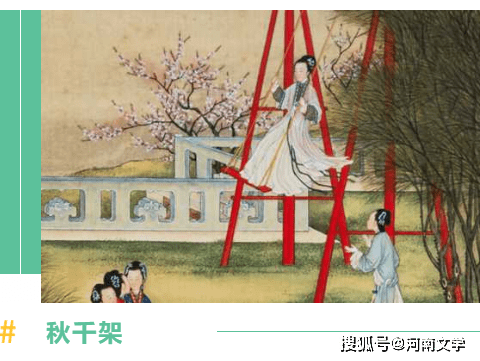
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缭乱送秋千。每当看着柳树上悬挂的秋千,暮春风一吹,我已听不见女郎银铃般的笑声,只见纷繁的柳絮满院飘飞……似乎苏东坡就在如许的季节,面临秋千,写下《蝶恋花》:
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边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门外汉,
墙里佳人笑。
为何行人耳闻笑声而目不见佳人?在苏东坡想来,就因为脚下的“道”欠亨“秋千”的脚前——秋千与行人之间砌着一道世俗般安稳的“墙”,所以“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安适情理。
所以,要想共荡秋千,与佳人共赏春光,就得拿出张生跳西厢的胆略,勇猛地踏进门往——纵使很快原路返回,青春也留下动感的记忆。晚唐诗人韩偓所描写的秋千诗句,就不时想得玉堂前的那位“娇羞不愿上秋千”的少女,见客进来和笑走,对他腼腆可掬。成果呢?似乎前景不妙,从他另一首诗中约略见出:夜深斜搭秋千索,楼阁朦胧烟雨中。佳人不在,秋千孤寂雨中,手把秋千绳的韩偓,深夜了还痴痴凝看朦胧的楼阁。看来坐不成墙内的秋千,只能做墙外的行人。那也客看看出韩偓的诗风,固然多写香奁的艳体诗,豪情倒也真诚。联想到他十岁时写诗,竟让情歌王子李商隐由衷发出“雏凤清于老凤声”、后来居上之赞。看来小名冬郎的韩偓生成就是贾宝玉式的“不克不及忘情”的小情种。
但要想荡秋千的立马做出反响,想定是意中人扑进院中。宋人李清照就“揭露”过“见有人来”的少女,蹴罢秋千后的脸色: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含羞地走到门口,却回头口嗅青梅……让人既想到“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名句,也想起林和靖娶梅为妻的史实。看来为时不远,秋千架将荡起两小我的体重。
当然秋千架荡的不满是欢笑,也有泪水。李商隐就描述过一位,“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往踏青,芙蓉做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未曾卸。十四躲六亲,悬知犹未嫁”的女子,成果“十五抽泣春风,后背秋千下”的凄婉遭遇。从李商隐的命运说,那何尝不是他的小我写照,“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不曾开”。
记得1999年,拜读余秋雨大著《霜冷长河》的那篇代跋文《秋千架》,觉得余先生是用八千字为他喜获“亚洲最标致女人”的老婆歌功颂德;实正与秋千的关系是不大的,所以我的印象也不深。
记忆深入的却是上引苏词《蝶恋花》,说被贬南荒的苏东坡,一日要相随的侍妾朝云弹唱此词。朝云歌喉呜咽、泪湿衣巾,东坡问其故?朝云低答:奴不肯唱者,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边何处无芳草也。
是啊,“天边何处无芳草”谈何随便,像余秋雨夫妇那样,秋千架上荡着甜美恋爱的事实是少数。所以我看着院内的秋千,日晒雨淋、絮飞花坠,在岁月的风中,好像钟摆,摇走孤单的流年。
记得朝云逝后,东坡再不复倾听此词。东坡是在用“静音”的体例,无声地祭奠芳草般的那人……所以,每当夜深人静,我似乎看见秋千架上,正依偎地坐着东坡与朝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