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思量疑陈寅恪,有没有不读先秦两汉经、子之书的“国粹巨匠”
九十年代以来,闻论理学者陈寅恪不断被媒体尊称为“国粹巨匠”,是“令郎中的令郎,传授中的传授”,是文化界炙手可热的人物。陈寅恪的学生,复旦大学传授汗青学家蔡尚思认为,陈寅恪不是“国粹巨匠”,而是史学巨匠。
面临陈寅恪被很多人尊为“国粹巨匠”,大事鼓吹,蔡尚思专门写了篇文章《陈寅恪不是“国粹巨匠”》。蔡尚思量疑陈寅恪,有没有不读先秦两汉经、子之书的“国粹巨匠”?

陈寅恪其时是清华学校国粹研究院的传授兼北京大学国粹研究所的导师,蔡尚思是北京大学国粹研究所的研究生,听过陈寅恪的课。蔡尚思认为,陈寅恪不是全读多读《二十四史》与《十三经》的学者。陈寅恪讲过,“生平不克不及读先秦之书”,“不敢治经”,“不敢看三代两汉之书”,“周秦诸子,实无足称”,“今人盛称周秦之国学,实大误”。在蔡尚思看来,周秦诸子是中国思惟文化的老祖宗,不认同陈寅恪的看点。
蔡尚思的学生王春瑜记述蔡尚思的一次谈话,“中国的国粹巨匠只要三个: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必然要说有四个,只能牵强加上胡适。如今陈寅恪被大大圣化,其实他也不是国粹巨匠;固然懂很多门外语,看了很多外国书,但中国史乘、文献,仍读的不算良多。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世界文明无出释教其右者,那是什么话?”(《苍龙日暮还行雨——忆蔡尚思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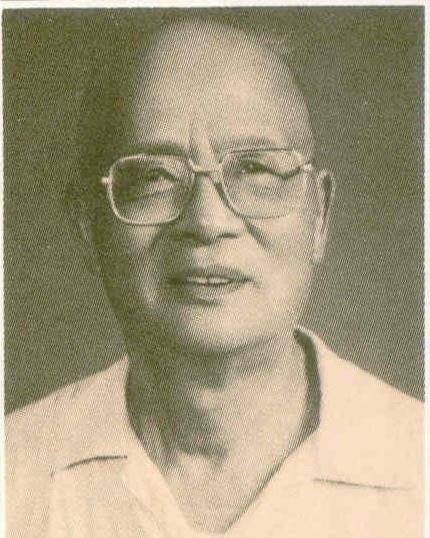
展开全文
蔡尚思是闻论理学者,有人将他与钱钟书并称,有所谓“北钱南蔡”一说。蔡尚思也是博学之人,“所读中国古书又不知多达几何”。早在20世纪30年代,蔡尚思先生还只要31岁的时候,闻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对他的博学赞扬有加:“读别集至三千种,并其他著作垂四万卷,自三代载籍,先秦诸子,以逮近今……”并称蔡尚思先生“学盖无所不窥,故能语无泛没,悉有分寸,汰其成见,避厥笼统……确实苦心孤诣,戛然独造”。
陈寅恪是史学巨匠,那在学术界是公认的,不单单是蔡尚思的观点。
冯友兰在《驰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寅恪先生用近代史学的办法,研究他所掌握的丰富史料,使中国的汗青学远远超越封建时代程度,他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创人或此中少少数人之一。”

陈寅恪的门生季羡林说,“先师陈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巨匠,学术文章辉耀寰宇,为国表里浩瀚学者所钦慕。”(《从进修条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畴和路子》)
葛剑雄在《我看陈寅恪现象》中直抒己见,“陈寅恪被称为史学巨匠,天然是当之无愧的。但称他为巨匠不是为了给他一顶桂冠,更不是为了编造他的神话,而是要实正必定他的学术成就和奉献,并赐与客看的评判。”
陈寅恪在1932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所写的审查陈述中曾自称: “寅恪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惟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曾国藩)、张南皮(张之洞)之间。”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范畴根本上在,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异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典范回纥译本之研究、释教典范各类文字译本之比力研究、蒙古满洲册本及碑志与汗青有关系者之研究。
陈寅恪在回国前写给妹妹的信即闻名的《与妹书》中表达了本身的治学纲领,“我所重视者有二:一汗青,(唐史西夏)西躲即吐蕃,躲文之关系不待言。一释教,大乘典范,印度少少,新疆出土者亦细碎。及小乘律之类,与释教史有关者多。”
在清华国粹研究院期间,陈寅恪次要努力于“中古释教史研究”,讲课也不太受欢送,有人曾如许总结道:“总起来看,梁(启超)、王(国维)都在研究院中有影响,而陈(寅恪)几乎能够说没有。概想起来,大约因为那时陈讲的是年代学(历法),边陲民族汗青语言(蒙文、躲文)以及西夏文、梵文的研究,太偏僻了,很少人能承受。”

蔡尚思强调,陈寅恪是多国多种的文字巨匠而不是国粹巨匠。季羡林感慨陈寅恪“博学多能,众多无涯”,“专就异族和外国语言而论,数目就大得可看”。季羡林研究陈寅恪的读书条记说:“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寅恪许多进修条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躲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等,算是东西语言。梵文、巴利文、印度古代鄙谚、躲文、蒙古文、西夏文、满文、新疆现代语言、新疆占代语言、伊朗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等等,算是研究对象语言。”(季羡林《从进修条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畴和路子》)
史学家汪荣祖在《陈寅恪评传》中认为,陈氏在民国史学上的更大奉献,仍是考据学上的功效。而陈氏能用一二十种外语,做为治史的东西,其成就势必超越。何况陈氏留学西洋,遭到西方语文考证学派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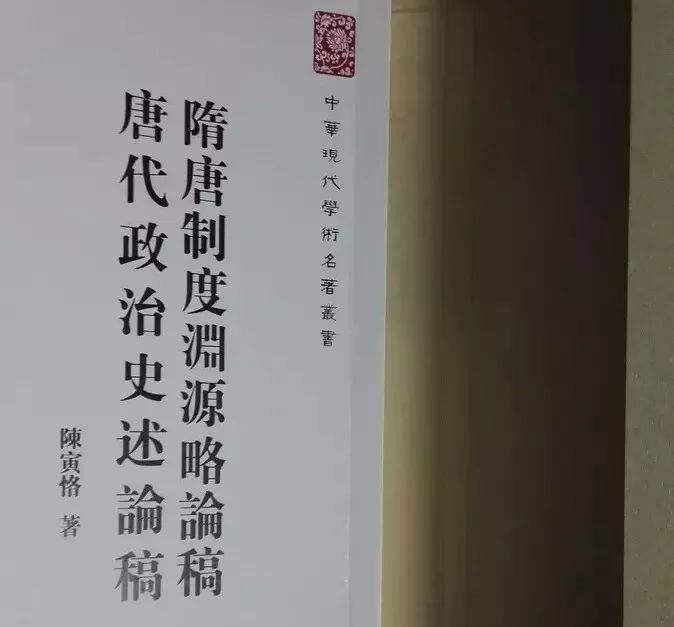
陈寅恪的次要学术代表做就是《隋唐轨制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以博学记忆力超凡被人称颂为“活字典”,那种超凡才能与学术成就是两码事。如今的问题是,陈寅恪被媒体给神化了,陈寅恪似乎成了无所欠亨的国粹巨匠。连国粹的定义都没有同一的定见,更不要说什么国粹巨匠。国粹巨匠酿成一个大坑,什么都往里填。
现代学者萧功秦认为:我觉得如今的常识界把陈寅恪过于神化了,陈先生是学院派,是个博学型的大学者,但他有学术而欠缺思惟,只要思惟才气具有那种对需要阐明的汗青的统摄力,以及对汗青大势的洞察力,而博学型的学者,却无法籍助于思惟与理论,把他看察到的工具予以深化的理解。(《陈寅恪为什么没有写出中国通史》)

季羡林在1988年“纪念陈寅恪传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陈先生是学术巨人,在他范畴之内,无法超越,原因就是我们此后不成能有他那样的前提。”
葛剑雄用事实反对季羡林的神化,“包罗陈寅恪如许实正的巨匠在内,他们的学问也不是没有限度的,他们的奉献一般也只集中在某一方面。像陈寅恪研究的隋唐史,我认为目前的整体程度已经高于他颁发过的论著。今天的隋唐史学家假设还停留在那样的程度,就没有资格当巨匠了。”(《我看陈寅恪现象》)
中国人最擅长造神,陈寅恪不外是此中的一个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