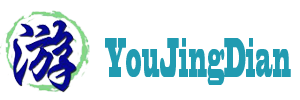齐国的臣民都思疑匡章,齐王为什么就是相信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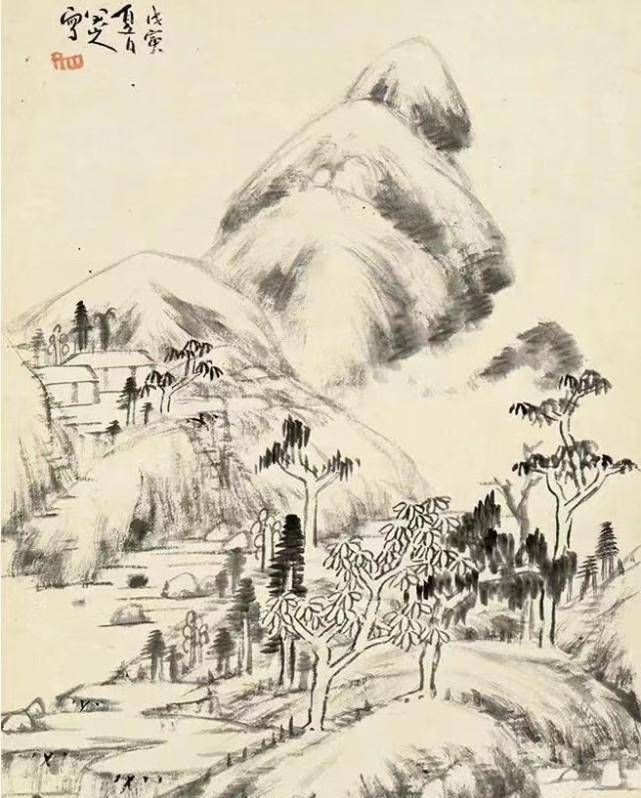
秦国向韩国、魏国借道往攻打齐国,齐威王差遣匡章率兵进击秦军,和秦军对垒时驻扎下来。
原因可能是齐国进侵燕国,诸侯兵援燕国。别认为诸侯发善心,只是在秦国的首肯下诸侯不想突破各国的力量平衡。
秦军、齐军两边的使者屡次来往,匡章变动了军服等戎行用的徽章,以便和秦军稠浊。
匡章操纵战前的空隙领会秦军,“为变其徽章”,是为了出其不料乘人之危。那种奥秘的战斗预备只要背后停止。
齐国的侦查兵报告请示说匡章把齐军纳进秦军,齐威王没有理会。没过多久,侦查兵又报告请示说匡章率领齐军投降秦军,齐威王没有理会。如斯如许三回。
仕宦向齐王恳求说:“说匡章松弛的人,如出一口,大王为什么不出兵进攻他呢?”齐王说:“他明明不会叛逆我,为什么要往进攻他?!”
齐王认为匡章是忠心的。所以前线的报告请示,齐王不听;官员的劝导,齐王不睬。
没过多久,侦查兵报告请示说:“齐兵大胜,秦军大败。”于是秦王以西藩之臣的礼仪向齐国赔罪。
自从秦孝公变法以后,秦国日益强大,为西方霸主,齐威王固然也强势,但二国不交界,互相威胁不大。“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谢于齐”,只是书写者的强调之词,为了展现匡章的战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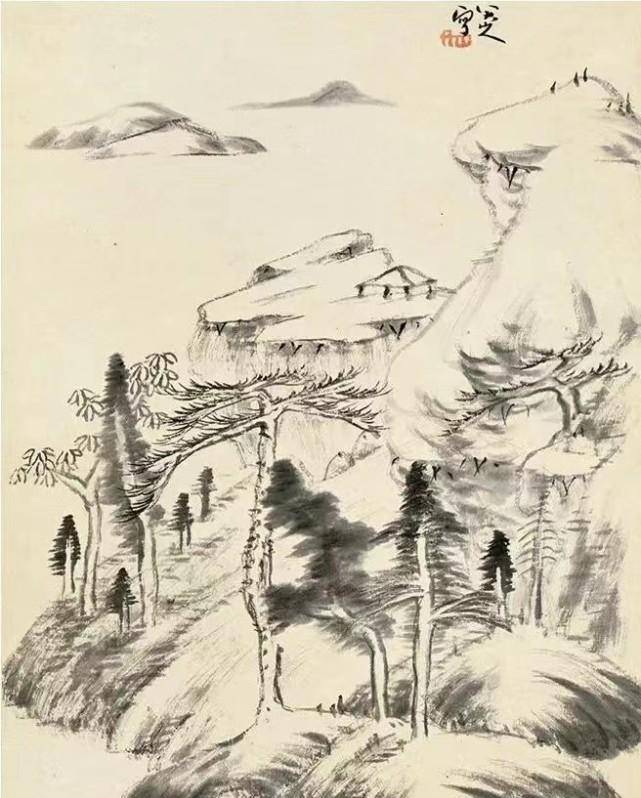
展开全文
齐王身边的大臣对齐王说:“大王怎么晓得匡章不会变节?”
大王有先见之明。错误地责备匡章,不影响臣子们诚惶诚恐地拍齐王的马屁。
齐王说:“匡章的母亲启得功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杀戮他的母亲,埋在马棚的下面。
我号令匡章领兵时,鼓舞他说:‘凭您的固执,戎行不受损伤、成功回来,我必然从头埋葬您的母亲。’
匡章说:‘我不是没有才能从头埋葬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启得功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没有留下教导就往世了。没有父亲的教导而从头埋葬母亲,就是侮辱死往的父亲,所以不敢如许做。’
匡章做为儿子不侮辱死往的父亲,怎么可能做为臣子侮辱活着的君王呢?”
先前,齐人对匡章的道德评判不高,“通国皆称不孝焉。”(《孟子•离娄章句下》)虽然孟子认为匡章的言行举行完全契合孝道,但国人普及认为匡章不讲孝道。
忠、孝是一体两面。能够必定,齐王没有吠形吠声。他从与匡章能否从头埋葬母亲的讨论中得出结论,匡章是一个忠心的战将。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那是其时人们关于社会生活次序的一种配合熟悉,是封建社会的文化产品。君王以此来抉择、要求臣民。
因为齐王具有识人的能耐,任人唯贤、用人不疑,匡章的一片忠心才有了闪现的时机。
东汉开国名将冯异与赤眉军会战时,让精兵穿戴和赤眉军一样的衣服,暗藏于道路两侧,大战之中择机而出,使得赤眉军难辨实假,惊慌溃败,最末冯异大胜赤眉军。
那就是对匡章“为变其徽章”的运用,那一战法在后世也不断延续。